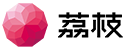介绍:
粉条的故事
厉建收
粉条,顾名思意,就是用地瓜、土豆、绿豆等等植物的淀粉加工而成。
至于是哪年才有的粉条,说法不一,时间也不一样。有说六百年,有说一千四百年。发明人也无从查证。反正,不论是哪年,是谁发明,这都是老祖宗用大智慧创造出来的。在大中华饮食文化中,是一道无与伦比的美味。
我的家乡盛产地瓜,这地瓜也是做粉条的最佳原料。就因为有这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每到冬天家乡至今有做粉条的传统习惯。也是加工过程过于复杂,才会盛产出这个上佳美味。原料得经过:清洗、剁碎、磨桨、打糊、提粉、漏粉、拉锅、理粉、泡粉、挂晒。以精湛的技艺,环环相扣的顺序,最终才会制成完美成品。
成品后的粉条,暗白光亮,缕缕银丝,相互缠绕有续,又不失典雅大度。做熟后,更是通身晶莹剔透,叨在筷子上似一根根玉丝,叮铃,滴答,闪闪发光。让人垂涎欲滴,会急不可耐吞进嘴里,口感爽爽滑滑,还不等咀嚼,它就像长腿一样,自动滑进喉咙,咕咚一下跑进胃里。此刻,立马勾得食欲大开,恨不能一口吃它一大碗。
小时候,家乡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在年三十的这顿晚饭,除尽可能做上一桌可口的佳肴外。粉条、猪肉、大豆腐炖大白菜是一道不可缺少的主打菜。这一道菜也是一年当中最最盼望和期待的,因为,一年中就这时才会放上猪肉。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钱也少,很少能有猪肉吃。也是在这一刻,一家人团团圆圆围坐在炕桌前,碗里盛上大米饭(这个平时也是少有的),米饭上面再舀上这道主打菜。那个味道呀,美轮美奂。猪肉的香,大豆腐的润,粉条的滑,大白菜的鲜,再扒上一口香喷喷的大米饭,那个香甜、那种鲜美,妙不可言,胜过山珍海味。
大人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粉条吸到口边发出唏哩、叭嗒的响声,脸颊上的汗珠滴进碗里也顾不上擦,大块朵颐的狼狈样。便忘却了一年的疲惫,享受着这天伦之乐,美滋滋的,乐在心里,笑在脸上。端着小酒盅,放在唇边很是惬意的嗞嗞吸着美酒,发出的声音就像是在说:乐、乐。又像是凯旋的欢奏续曲。再就着美味佳肴,啦着一年来丰收喜悦的话语,最是温馨和谐,其乐融融。
晚饭后,孩子们就会提着自已制作的小煤油灯笼,跑到大街上找小伙伴们玩,或者到本家给长辈们磕个头,道一声过年好。有一年,在出门时,遇见本村一徐姓老者,他愁眉苦脸很是难受的样子,手不住的拍打着自己的肚子,口里一个劲的嗳呦着,在大街上来回走。我好奇,上前问之,这时,他一扫愁容,眯起眼睛,笑嘻嘻的对我说:“大弟,哥哥吃多了粉条炖猪肉了”。原来如此,美食不可多用呀。而此时的他,谁又能说,他不是吃饱了撑得才满大街走呢?!!
六七十年代家乡接待客人的最高规格,讲究五碗四盘,合起来即是九个菜。里面有一个碗里的菜就是粉条,粉条是长长的。这些,其意义大概就是:五谷丰登,四季平安,九九长远,健康长寿,客人长来长往,也是向往美好的愿望吧。
那些年,家里要用烧草做饭。生产队分的草不够烧,学生放学后,都会相约到坡里拾草。一般拾满提篮后,都会在坡里玩上一会。我们还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出门时各自带上一样东西出来吃。那时也没什么东西可拿,无非就是,你拿一把大豆,我拿一把花生(这两样当时可是奢侈品),再就是地瓜土豆什么的。那天我是拿了粉条。因要过年了,父母刚用地瓜换了两斤粉条。我们把各自带的东西拿出来,放在一起。拿一块铁皮,再用三块石头支起铁皮,下面点上火,把大豆或花生放在铁皮上面烤,地瓜土豆则直接放进火堆里烧。
这一切还有个好听的名字,美其名曰:烧肴。那大豆在不断加热后,叭叭叭的叫响着,并在铁皮上面你争我抢跳起欢快的舞蹈。粉条则是用手拿着,直接在火苗上面燎。粉条遇火后,就会发出嗞嗞啦啦的声音,像是为年轻人弹奏着欢欣的乐符,同时还会冒出一股股青烟,跳跃着蹿起红红的火苗,火树银花,煞是好看,空气中又会弥漫出芬芳诱人的香味。粉条在鼓胀起来后,就可以吃了,趁热放进嘴里会有烧过的燎烟味,热热的,脆脆的,软软的,香香的,那个好吃劲,别有一番风味在心头。
母亲给我做了一条新棉裤,也是第一天穿。烧肴时,也不管干净如否,跪在地上燎粉条。正在热火朝天的忙活,也准备品尝佳肴时,突然感觉右腿膝盖处痛疼,抬腿看时,已烧出了一个大窟窿,而且还正在得忘形的燃烧着。冬天的地是冰冻的,沟里的水也已结冰。没办法,大家只好搁置起美肴,先合力用手尽可能多的划拉细土,人多力量大,费了好大劲,才把得意洋洋,似无忌惮燃烧的火捂灭。
回家也不敢说。要知道,那时能穿上一条新棉裤,不亚于现在买一部苹果七的手机。当然,最终还是逃不过娘的眼睛,还好,娘没打我,娘只是默默的补上了一个大补丁。这都是粉条的“功劳”,不是吗???
春节就要来了,又到吃粉条的时节了,好想回老家吃粉条,回到老家能找回童年吗!
大家还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