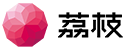介绍:
上个月,病房来了一个晚期重症病人,陪他来的是他的弟弟,病人不太好沟通,有智能不足的问题,连哪里痛、要不要喝水这般简单的问题都说不清楚,要靠他弟弟转达。从四肢的蜷曲和走路的样子判断,应该是长期待在家里,没有得到专业的照料。他弟弟总是皱着眉,不是快乐的人,身上背负着不幸的印记。
我也是不幸之人,能在人群里嗅出相同气味的人。也只有像我这样不幸的人,才能对生死如此无睹,视之淡然。在护校毕业前夕,我就立志要进入安宁照护(临终关怀)的领域,这是一个绝望的地方,你看不到病患有好起来的一天,只有日复一日的崩坏。有学姐做了半年之后,彻底弃守这个行业,生死的
反馈太大,没人承受得起。
这一行的每个人,都会记得自己接手的第一个病患过世时的各种细节。肝胆科的小文,她记得那位车祸病人过世时,血溅了她一身。也不是都这么惨烈,心脏外科李美的第一位死去的病人,是一个和蔼的老太太,过世的时候,李美正在交谊厅(摆有沙发、桌子和电视,住宿学生可以翻翻报纸、聊聊天、看看电视的地方)看《康熙来了》,从此她有一整年不再看这个她曾经最爱的节目。内科的阿迪,第一个病人过世,她正在削笔;外科的年年,第一病人过世,她在 key-in(录入)资料……
唯有对外在的生死麻痹,才能在这样的环境存活,她们习惯不表现情感,喜怒哀乐从不在心里留下痕迹,她们表情木然,久了颜面神经也懒得动了,再
高兴的事,再悲伤的事,也就这样埋在脸皮底下了。
我跟大家不一样,我不记得我手上第一个走的病人。母亲常说,你这个小孩儿,天生无情,没血没泪。这像是一道解不开的诅咒,我几乎不记得为什么事哭过,或为什么事彻底开心。像我们这样不幸的人,医院是最佳的躲藏处了,我不会因为病人崩坏的身体而难过,不会因为病人离开而整日低潮。
医院,有死人的医院,是个适合没有情绪的地方,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能存活下来。没人愿意到安宁病房,我无所谓,并不是我比较伟大,我只是,无所谓而已。
我看过各种惨烈的人生际遇,好一点的,就是躺在床上,在某个夜里,哀号几声,家人在他耳边放他喜欢的老歌,
推着病床,哐当哐当,下了电梯,回家断气。我值班的时候,总是听到长廊上哐当哐当的推床声音,那像是死神的预警铃,又有一个人要走了。
当然,偶有“喜剧”发生,有位老太太,孤家寡人住了进来,有天跟照顾她的护士道别,谢谢她的照顾。当天晚上,老太太血压、心跳趋疲软,医生判定是弥留了。我们推她下了电梯,外佣接她回家了。照顾她的小柯是新手,几乎就要在门口哭了出来。隔天,老太太打电话来跟小柯聊天,她没死。小柯五味杂陈,是要气自己白哭了?还是替老太太高兴?但这种高兴也很虚假,她终究是得走的。三天后,老太太断气。小柯没掉一滴泪。好像我们在这场喜剧里,重新适应了死亡。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上个月十二床的黄先生,住进来已经一周了,他刚结婚,有个三岁的儿子,鼻咽癌晚期,口鼻变形。黄太太说,老公是个严肃的人,长年在外地工作,小孩儿出生后,他没抱过几次,生病之后,他有天把脸凑近沉睡中的儿子,他想起,自己从来没吻过他,想亲昵地把脸枕在儿子柔软的腹部,好好闻闻婴儿身上的味道,他要记住这个味道,好让自己一人走在黄泉路上不那么孤单,不那么害怕。
他想着离开之后,儿子还会记得他吗?会不会记起父亲,只有刺鼻的药味,和身上器官败坏的腐臭味?想着想着,他竟细细哭出声,儿子从睡梦中醒来,看见父亲迫在眼前变形的口鼻,和呼吸道溃烂的恶臭,童话里的巫婆魔鬼地狱,也不过就是如此。
三岁幼儿承担不起,放声大哭。
从此,黄先生不再抱他的儿子,他暴躁地向妻子发脾气,他们的病房时不时传来黄先生摔东西的巨响。三周后,黄先生过世,我在病房外,遇到来收拾行李的黄太太,她儿子拉着妈妈的衣角说:“生病的大野狼走了吗?我们快点回家吧。”
人世最大的不幸便是,曾经是那样爱过,下一刻却恒久地被抛开。黄先生是如此爱着他的儿子,却被童稚的眼光狠狠地伤害,他连弥补的机会都没有。他的儿子日后也许还记得这段模糊的记忆,并为这段记忆深深遗憾。
我在这对智能不足的哥哥与陪他的弟弟身上,也看到这样的遗憾。弟弟不多话,只是天天帮哥哥换上新袜子,上面是与病人年龄反差很大的卡通图案。我告诉他,病人的脚畸形,包裹太密合,
容易发疹子、溃烂,尤其癌末了,免疫力又不好,易感染。弟弟总是 低头说抱歉,下次见了仍是帮他哥哥穿上袜子。
之后,我不再说了。我明白,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不能只想到病人的生理病痛,还要想到家属的赎罪告别行为。
可以赎罪,总是好的。
我喜欢值小夜班,下班后,走在没有人的路上,心里特别宁静。黑色的柏油路浓得像墨汁,快滴出水来。带月光的晚上,柏油路又是另一种黑,像夜里的海洋,闪着暗暗卷来的浪花。
我不喜欢有月光的夜晚,所以刻意把夜班排在月底或月初。月光从来不是浪漫的事,走在路上,月光一波一波地扭动,我记起那个晚上,那些事,总让我胸口一闷,喘不过气来。
大家还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