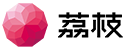介绍:
提问7:两位先生好,赵园老师反复提到物质文化研究,我上个月刚从苏州中研院做一个江南文化研习营回来,二位先生的书都在中研院。我有一个问题想问赵园先生,关于文学史和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我们去处理具体的历史问题时,都是具体的,当初是具体的,比如文学、人的问题,虽然是具体的,但人会常常受到更长远的一种历史影响,比如在年轻时期很多人抒写陶渊明,可能跟这个时代有关系,可能跟整体文学的纵向也有关系。梁启超先生说文学史不能讲明代或者清代的文学史,因为文学史的脉络跟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我想请教您的,当您在处理文史和历史材料时,如何把握材料,尤其是文学材料中的问题?有的时候受到具体历史事件的影响,可有的时候作为人来说不是完全被动的状态,可能也有一些反思。
赵园:我读的好多应该是文学材料,但没有进入文学史,也没有被各种文选接纳,因为士大夫的文集收入的散文、诗,那些都是文学作品,那些文学作品只不过没有进入到某一个档次或者一个等级流传下来。我主要依赖文集,依赖的也可以是文学作品,我把它当史料运用的时候,当然是根据我自己的选题,根据我自己设定的话题里做的选择,所以,可能在运用中就和文学史的运用很不同。主要是我没太弄清楚你的问题,我找人救我一下。
杨念群:我帮你回答一下,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赵园老师处理话题或者处理人物时,牵连周围的制度、环境和一些背景制约,在单独处理人的话题时,有时候反而难以处理背景、制度和环境制约的层次问题,或者两者之间发生一些纠结和发生一些冲突,是不是这个意思?
提问7:不完全是,我是更考虑到文学本身的逻辑问题,文学的逻辑和历史逻辑有什么共同,历史的逻辑完全受到制度和环境的制约,可文学的逻辑有时候不是,比如追慕前代某一个人或者追慕历史中的某一个感觉,会抒写一些东西。反映到文学作品中,二者间既有历史的、环境的、政治的、制度的影响,但同时内心又有作为文人、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想,我想听您处理这两个现实与理想之间关系的想法。
赵园:这个问题好像分得很具体才能够回答,否则原则的含义很难。文学确实如你所说,很多是超越了时代或者超越了某个具体事件,我们如果把它当做某一个事件的注释是有问题的,应尽可能避免。所以对于正史的理解,肯定是有限度的,因为文学有自身的传统,也有一整套的长期形成的修辞方式,这个修辞方式,不一定是属于某一个非常具体的时空,如果是把文学的表述当做某一个具体事件的一种材料,那么在使用材料方面就得非常谨慎,认识到它的限度。但这个问题需要更具体化,哪些材料能够这样用,或者应该如何用,涉及的是这样的。
谭徐锋:可以这样理解,是不是以文学方式还是以史学的方式进入,文学史的感觉更强一点。比如赵老师处理明清之际这本书,有话题有问题进入时,文学和史学的紧张感不知道怎来写,有可能文学的立场稍微多了一点,但没有说做文学史,就关注话题,以话题方式切入,各个视觉、角度更丰富一些。
杨念群:你问题的预设可能有问题,在具体里其实是模糊的,原来讲文史不分家,放在具体环境里哪个是文哪个是史很难表述,比如司马迁《史记》有很多场景的呈现是文学呈现,但我们当历史看,因为他也没有经历,比如鸿门宴,项庄舞剑如何,他不知道,这是历史还是文学?但如果放在史记脉络里,从司马迁角度看,就是一个历史。
赵园:文史在中国传统中,从来都没有那么截然地区分,所以不但司马迁是文学大家,欧阳修还修五代史,这些史书的传记部分,多数都是人修理德国,因为别人考证不清楚,明史馆的构成,谁撰写了哪些篇很清楚,都是大文人。而且,说实在的,他们使用材料比我们现在更不严格,太不严格了,有时候真是把那些传闻如不稽之谈、神灵鬼怪都写进去了。你说算是史料呢还是文学呢?我觉得运用之妙在于一心,主要看你是怎么运用的,而且是在什么意图下运用的,神异灵怪那些古怪的东西,如果在研究社会心理意义上运用的,当然很有意思,当然可以作为材料。要跳出非真即伪的框子,那么史料就可以打开。现在好多讨论的并不是事实是那样的,而且现在我们对于事实、对于真相,包括对于历史,运用这些词时都是加上引号,因为现在历史观念变化了。
杨念群:什么叫真实,完全是现代的概念,什么叫历史真实?实证主义那些是真实吗?不对。历史研究的评价也有很多问题,比如顾颉刚说大禹是虫子,顾颉刚就从科学主义角度讲,大禹是虫子不行,大禹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虫子。大家后来都认为大禹虫子,利用大禹是虫子这样很多的事情,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大禹是虫子就是历史的真实,而且有文义,背后赋予意义后,后人赋予意义的过程中就变成了历史事实,如果从科学主义角度,全部都不是真实的,那历史就没法做了,就跟赵园老师说的志异鬼怪一样,志异鬼怪一旦进入话语系统被赋予意义,就变成真实的了。所以现在很多搞历史不行了是因为没有想象了,用科学主义界定真实怎么可以?写出的东西没法看,枯燥、无味、论文体。
谭徐锋:这是杨老师的感觉主义。
提问7:现在心态史领域、观念史领域在上升,跟这个有关系。谢谢。
赵园:但要相信有事实有真相,如果连这个也不相信,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一定要努力地逼近真相,找到事实,如果此一时彼一时,什么事情都是建构出来的,那是更大的问题了。
提问8:谢谢两位老师,不是历史专业出身的,问的问题可能有点外行,赵园老师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张明扬的问题,这种心态和变化,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灵活性,对民族性有影响,您并没有谈到对民族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我读的历史不是很多,但我不太能接受在历史的叙述里,运用民族性,我觉得民族好像是比较笼统的概念,想请您具体说说影响。
赵园:尽可能不用“民族性”的说法。张明扬问到,我是拿中国人跟日本人做比较,很多情况下日本人不会给自己留这么一条后路,中国从来是有经有权,“权”是灵活性,一定要有原则,但一定也要有灵活性。我最近做父子,要为子孙留出一条生路。比如傅山父子,虽然儿子死在父亲之前(据他父亲说,因为抑郁、压抑就早死),但更多的遗民是放他儿子一条生路,找了一些理由,比如“遗民不世袭”。别的时候也是这样,如“忠孝”,中国民间说忠孝不能两全,不能去抗敌:母亲老了,要为母亲养老送忠。日本人在有些场合可能不会给自己这么大的灵活度,这可能是我们对东瀛有点区别的地方,但我想各有利弊,确实造成了我们跟东瀛之间的不同,包括文化尺度、文化标准,但有时候我也怕我们那种过分习惯于用权的态度,这是有问题的,使得坚守更难,使得开脱自己的不坚守更容易。我看有人写了一连串的问题批评犬儒主义,有些地方很对,但没有追溯到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肯定有这样的东西,使得我们可以有很多理由摆脱责任,使自己不坚守,为自己的没有操守辩护。我那儿用了“民族性”的说法,我愿意修改,尽可能不用这个词,这种说法容易招致误解,而且这种也容易跟五四国民性的说法有较大分歧。谢谢。
谭徐锋:谢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再提问,大家有问题可以私下跟两位老师交流。之所以选历史记忆作为这场的讨论主题,我想有学术的主张,从生活史、心灵史的角度切入,会不断发现新的历史视野,取得更多丰硕的历史发现,让读者得以更深入地理解当时的历史,而且这种丰富性与可能性会使原来枯燥乏味、模式化的历史认识变得丰富多彩。
讲座开始前,我跟杨老师聊天,问他回到哪一个朝代会更好一点?他说回到晚明,会不那么郁闷。我想晚明可能也是一种丰富的痛苦,因为晚明的读书人也惨得不得了,毕业即失业,秀才举人找不到饭碗的很多,当时市民文学那么发达可能跟这个很有关系。那是一个值得不断回眸的时代,但痛苦与迷惘也俯拾皆是。而当下,我们对近代的历史记忆也在不断复活,我们当下怎么坚守自己的历史记忆,这里面需要定力与坚持,保留一份对真相的好奇心,值得予以再三致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