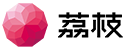介绍:
按:“赤裸的人在赤裸的大地上”,在这个静谧的夜晚,我给你看见“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说她是“哀泣的缪斯”,她的一生中有无数情诗,然而我要读的,却不是这个。为什么呢?
阿赫玛托娃的爱情诗当然首先只是诗。除了别的东西,它们具有一种酷似长篇小说的特质,读者可享有一段美妙时光去详细分析它们的女主人公的种种苦恼和折磨。(有些人就是这样做的,并且在这些诗的基础上,公众发热的想象力还进一步使它们的作者与亚历山大·勃洛克——那个时期最著名的诗人——以及与皇帝陛下本人发生“罗曼蒂克的关系”,尽管她是一个远比前者更好的诗人,而且比后者高了整整六英寸。)半自画像、半戴面具,它们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会以剧场的致命性扩张一出实际戏剧,以此探索她本人的可能极限和痛苦的可能极限。较快乐的状态也会成为同样的探索对象。简言之,现实主义被用作通往形而上学目的地的运输工具。不过,如果不是因为处理上述情绪的诗数量如此之多,则这一切只能说是活化了爱情诗的传统而已。
这个数量既拒绝传记式分析,也拒绝弗洛伊德式分析,因为它超越了受话者的具体性,把他们变成作者说话的借口。艺术与性爱的共同点是,两者都是我们的创造能量的升华,而这使它们都没有等级制。阿赫玛托娃早期爱情诗的这种近乎怪癖的持续,与其说是激情的反复出现,不如说是祈祷的频率。相应地,不管这些诗的叙述者(想象的叙述者或真实的叙述者)多么不同,它们都展示一种风格上颇大的相似性,因为爱情这种内容都习惯于限制其形式花样。这同样适合于信仰。毕竟,适合于真正强烈情绪的表达形式,就只有这么多;说穿了,跟仪式差不多。
阿赫玛托娃诗中的爱情主题一再重现,不是源自实际牵涉,而是源自有限对无限的乡愁。对她来说,爱情实际上变成了一种语言,一种密码,一种用来记录时间的信息或者至少用来传达时间的信息的音调;只不过,她以这种方式更能听清楚那些信息罢了。因为最使这位诗人感兴趣的,并不是她自己的生活,而恰恰是时间和时间的单调对人类心灵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她自己的措辞产生的影响。如果她后来愤怒于批评家想把她简化成她的早期作品的企图,那也不是因为她不喜欢那个惯常地害相思病的女孩的形象,而是因为后来为了使无限之单调变得更听得见,她的措辞以及伴随着这措辞的密码都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
……
战前这十五年也许是俄罗斯整个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无疑也是阿赫玛托娃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正是这个时期提供的材料,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时期灭掉的人命,使她最终赢得了“哀泣的缪斯”这个称号。这个时期干脆以纪念诗的频率取代爱情诗的频率。以前,她乞灵于死亡,以死亡来作为这种或那种感情紧张的解决办法,现在死亡变得太真实了,使得任何感情都显得微不足道。它从修辞变成无辞可修。
如果她仍能继续写作,那是因为作诗法吸纳了死亡,也因为她为自己幸存下来而内疚。构成她那组《献给死者的花环》的诗,无非是企图让那些弃她而去的死者来消化或至少加入作诗法。不是她试图使死者“不朽”:他们大多数都已经是俄罗斯文学的骄傲,因而已经足以使自己不朽了。她无非是试图管理存在的无意义,这存在因为其意义的源头突然被摧毁而对她张开大口;她无非是试图使无限与一个个熟悉的影子栖居在一起,以此来驯化那应受谴责的无限。此外,跟死者说话是阻止言语沦为哀号的唯一途径。
……
在某些历史时期,只有诗歌有能力处理现实,把它压缩成某种可把握的东西,某种在别的情况下难以被心灵保存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整个民族都使用了阿赫玛托娃这个笔名——这解释了她的广受欢迎,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使她可以替这个民族说话,以及把这个民族不知道的事情告诉它。从根本上说,她是一位人类关系的诗人:爱惜、紧张、切断。她展现了这种演变,首先是通过个人心灵这个棱镜,然后是将就着通过历史这个棱镜。不管怎样,你能够利用的光学方法大概就这么多。
这两种视角,透过作诗法而愈益清晰,因为作诗法无非是语言内部一个装着时间的容器。因此,顺便一提,她才有能力宽恕——因为宽恕并不是一种由信条所认定的美德,而是世俗意义上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时间的财产。这也是为什么她的诗歌不管发表与否,都能留存下来:因为作诗法,因为这些诗充满了上述两种意义的时间。它们能留存下来是因为语言比国家古老,也因为作诗法永远比历史更长久。事实上,它根本不需要历史,而只需要一个诗人,而阿赫玛托娃正是这样一个诗人。
*节选自布罗茨基《小于一》
《离别》
一
我们经常分离--不是几周,
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
终于尝到了真正自由的寒冷,
鬓角已出现了白色的花环。
从此再没有外遇、变节,
你也不必听我彻夜碎嘴,
倾诉我绝对正确的例证--
源源不断,如同流水。
1940年
二
正象平素分离一样,
初恋的灵魂又来叩击我们的门扉,
银白的柳树拂着枝条冲了进来,
显得那么苍老而又那么俊美。
我们伤心,我们傲慢,又有些傻呆,
谁也不敢把目光从地上抬起来,
这时鸟儿用怡然自得的歌喉对着我们
唱出我俩当年是何等的相亲相爱。
1944年9月25日
《爱》
乌兰汗译
有时像一条小蛇蜷成一团,
偎在心田上施展法术,
有时在白色的窗台上
像只小鸽子整天不停地咕咕。
有时在晶莹的霜花里一闪,
有时又沉在紫罗兰的梦境......
但它准确而又神秘地
来自喜悦,来自宁静。
在惆怅的琴声的祈祷中,
它善于如此甜蜜地哭诉,
有时候会突然令人心悸:
在陌生的浅笑中把它认出。
大家还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