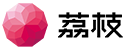介绍:
按:生活总是在别处,别处的生活总是会让人生出精彩之感。其实,生活是在细处,那么在巴黎,还是在北京,又或者在甘肃,其实都一样的美。
今天和你读于坚的巴黎笔记。
*正文*
我住的这一套房子有四个联通的房间,两个卫生间,一个厨房。从前,有一家人就在这里生儿育女,房间里到处是他们生命的痕迹,衣柜上摆着主人一家的照片,他父亲,他母亲,他五岁或者九岁,七十年代。还有从某地旅行带回的小玩意儿,令人沉思起来,他为什么带回这个,其意何在?从前带回它的冲动早已消失,其意不明。小玩意也老了,蒙着可以暗藏含义的灰。书架上还藏着一副拓片,明代的楷书。房间都很小,最大的也就十平米。每个房间都有落地窗,窗子打开就是阳台,已经多年未用,摆着些干掉的花盆和杂物。巴黎的房子大多是几何型的,各种三角、楔形和方形的组合,这种奇妙的组合倒解构了几何,成了方圆的了。这套房间连接在一起,是一个圆的四分之一,相当于钟表从12点走到15点,15点到18点是另一家。如果要进入18点到24点的房间的话,就要从后面那条街的另一道门进去。这些房间像迷宫一样,有的房间可以隐藏起来。开窗大约是法国建筑很重要的一环,与中国房子只在院子内部开窗不同。房间一定要和外部联系,仿佛方便可以随时逃走。西方电影里经常有破窗一跳的镜头,这一幕在中国传统建筑里是不可能发生的,人们只是跳到井里去。楼道中间那个旋转而上的桃花心木楼梯,似乎是这群房间的核心,但打开门进家,来到目的地,却来到了世界的表面。对面的楼房也一样,看得见那家的人在窗子后面活动,站在餐桌前整理花瓶,从卧室走到客厅……这个家给我的感觉不是进入到一个密封的内部,而是从内部出去,在一个界限中让世界看到自己而不可侵犯,就像在孙悟空为唐僧画的那个圈里。
小偷潜入一个房间是很自然的事,就像盐巴。这个世界怎么能没有小偷呢?那么多的窗子,那么多的阳台,那么多的后院。这些房间有一种哲学式的深度,它的设计是基于平等而不像中国传统建筑那样是基于尊卑贵贱,内外有别。没有中堂。不仅仅设计了安全舒适,也设计神秘感,被盗的期待,被窥视的担心,孤独、梦魇,俯瞰世界的居高临下,自杀的诱惑,囚禁感、抑郁症的契机、下楼重返人间世的犹豫不决、上楼时忏悔般的沉思、回到私人城堡的归属感、独享一隅的喜悦,无数的暗屉,某一个会找出已故外祖父忘记的镍币……是的,每次气喘吁吁地上到自家门前,开门进去,咔哒一声锁妥,再将做得非常精致的黄铜门扣搭好,内心的石头落地,就像肩头上扛着的一袋子大米重重地隔在厨房地板上。
先去喝口水吧。巴黎人很少喝矿泉水,自来水管的水可以随便喝,远古的水并没有在房间里中断或变质。阳台上可以看得见天空和远处教堂的尖顶,法国黄的房子一条街与一条街不同,在阳光的分派下,这个窗子外面的街是阴郁的灰白色,另一个窗子外面的街是乳黄色,像是一排奶酪。
我就像一个突然长大的儿童住在一个刚刚搬进去的房子里,好奇、紧张,穿过一个个房间,调整着过去的经验,准备着去孤独。孤独本来就是身体性的,每个人离开母体来到世上,就被抛进了孤独,人此后的任务是与世界建立联系。当这种联系成为陈词滥调之后,孤独就意味着一种精神状况,精神的自我解放,人自己人为地在精神上失去与世界的世俗的关系,进入一种超凡入圣的状态。精神的自由也意味着身体的孤独、封闭。孤独是一种语言的疏离状态,一种对陈词滥调的恶心。在巴黎,我失去了语言,失去了陈词滥调,我像一头野兽走出陈词滥调和习见的森林,开始用我的身体、感官与这个城市说话。这是一种诱人的孤独感,我在众人的轻车熟路中陷入迷途,什么都不知道,盲人摸象。但是我什么都知道,巴黎这头大象早已迈入世界原野,就像非洲荒野上的那些庞然大物,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它垂然站在世界之雾中。像一头象那样沉默,缓慢,巍峨而臃肿。巴黎表面喧嚣嘈杂,其实它沉默着。语言的丧失指引我以另一种方式进入这头大象的里面,那儿是沉默的,像一群已经失去了主人的老古董被遗产继承者(某种有资格的空间)收藏着。巴黎自己收藏了自己。有时候,在街头漫游的时候,会听到这头大象的一点儿低语。从巴尔扎克、雨果、左拉、波德莱尔们的字里行间或者夏尔丹、马奈、柯罗的笔触里传出来。
我毕竟置身异国他乡,许多情况需要适应,包括卫生间漏水;开关失灵,要找到关紧它的那个已经移位的灵在那里;厨房里没有圆底锅、也没有筷子、酱油、醋、味精等等。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上要学会分类,西方的器皿每一件都有看不见的直线、箭头指出的专业用途,这可不是一团乱麻,像在老家那样,道通为一,用一双筷子吃遍所有,面条、米饭、菜梗、花生米……就是粉末也可以用筷子撮。在这里,喝咖啡的杯子,喝水的杯子、喝果汁的杯子,喝牛奶的杯子,切肉的刀、切奶酪的刀、切面包的刀、舀汤的勺子、搅拌咖啡的勺子、吃甜食的勺子……都是不同的,而且各有其名,不是刀子、杯子、勺子就可以替代所有。THE控制着一切。你当然可以乱来,你是中国人嘛,你不懂规矩。什么逻各斯中心主义,没那么复杂,这就是。我以前在法兰克福一位德国教授家里小住,他甚至对我在面包抹了果酱、接着抹花生酱、再抹巧克力酱大为惊骇。你不能乱抹。如果在咖啡馆里的话,你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你桌子上那张方型餐巾纸的约40厘米×40厘米的范围,这可不是仅仅为了好看。你越位的话,大家也不会说什么,只是你的信用也就被暗中起着疑了:这位先生至少不是一位绅士。那个可怕的洗衣机外面印着法语,标识着各种符号,数字,就像一张施工图,我总是搞不清楚要怎么弄,有时候它突然转起来,有时候又打不开,把我着急穿的衣服关在滚筒里。不小心按了某个纽,它就开始加热,魔术般地将我的毛衣变短了一大截。总担心窗子没有关好,每次出门都要关一批窗子,总是要忘记某一扇。我日夜期待着一位小偷,判断他会从哪个窗子潜入,但他像一首被过度处理的诗中的神那样,没有来过。
哦 巴黎 你的小偷是一个藏在败屋后面的花园
在那里 谁失去了爱情 手表和傲慢
遗物招领处 在倒塌的长椅上 闪着微光
大家还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