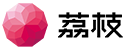介绍:
纽约与巴黎不同,与伦敦也不同。它不是斯波坎市乘六十倍,也不是底特律市乘四倍。它让所有城市望尘莫及。它甚至想法儿在大萧条最低迷的时刻,凌空达到了最高点。帝国大厦拔地而起,高达一千二百五十英尺,而此时,草木长出地面六英寸也是疯狂。(大厦顶部有一座飞艇系留塔,但从没有飞艇造访过;不景气的时候,需要雇人冲洗厕所;它还在大雾中给一架飞机撞过,无数次遭受雷击,时常有人想不开,从楼顶纵身跃下,以致行人经过第五大道和三十四街交界处时,都会下意识地加快脚步。)曼哈顿东西南北,再无可以扩张处,只有向高空发展。这一点,便是它气势恢弘的主要原因了。它对美国的意义,如同乡下教堂的白色塔尖——那是理念与信仰的实在象征,飞升的白翎呼唤,道路就在上面。夏季的游客,乘车晃晃荡荡驶过地狱之门大桥,在皇后区的鸽舍和后院上空滑行,从卧铺车厢的窗子眺望西南,第一抹晨曦投射在中城钢铁铸造的尖顶上,他能清晰无误地看见城市腾身而起:高墙与塔楼升高,烟雾升高,温度暂时还没有升高,千百万醒来的人们,希望和激情也在升高——如一柄犀利的长矛直逼苍穹。
纽约竟能运转,简直是个奇迹。事情让人完全难以置信。居民每日刷牙,得从卡兹基尔山区和威切斯特县山中汲来几百万加仑清水。曼哈顿的小伙子给他在布鲁克林的女孩儿写信,爱的信息是通过充气管道吹给她的——“噗”的一声,就这样子。电话线、电力线、蒸汽管、煤气管、污水管的地下系统,已经是个足够的理由,让人把曼哈顿岛丢给上帝和象鼻虫了。每次切开人行道,手术的噪声都吵得人毛骨悚然。按理说,纽约早就该毁于恐慌、大火、骚乱,或者循环系统某些攸关重大的供应管线的失灵,或者哪种莫名其妙的短路。城市早就该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瓶颈处,发生难以收拾的交通混乱。食品供应线若是中断,只须几天,城市就将饿毙。贫民窟流行或船只上的老鼠传播的瘟疫会扫荡它。海浪会从四面八方席卷它。每隔几天,从泽西吹来的烟雾,就像恐怖的裹尸布,大白天遮挡了所有的光线,大楼的办公室仿佛悬在半空,人们摸索,沮丧,只觉得世界末日来临,如此这般,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巢室里工作的人,怎能不精神失常。集体歇斯底里是一股可怕的力量,然而,纽约人似乎每次都能与它擦肩而过:他们坐在半途停顿的地铁车厢里,没有幽闭恐惧感,他们靠几句俏皮话,摆脱惶恐局面,他们咬定牙关,耐心承受混乱和拥堵,凡事总能对付过去。所有设施都不完善——医院、学校和运动场人满为患,高速路乱乱哄哄,年久失修的公路和桥梁动辄寸步难行,空气窒息,光线不足,供暖要么过头,要么差得远。可尽管麻烦不断,效率低下,纽约却以大剂量的维他命补偿了它的居民,这就是对一种独特的、国际化的、强大的、无与伦比的事物的从属感。外来人小住纽约,可能而且往往陷入一连串的尴尬、不便和失望:听不明白饭馆里侍应生的话;分不清哪儿是诓人的酒馆儿,哪儿是规矩的酒吧;进地铁搭错了车;为个小小不言的问题招公共汽车司机顶撞;街上的噪声吵得人一夜无眠。游客奔来纽约,尤其是在夏季——他们一窝蜂地涌向自由女神像,(城里的许多居民从不涉足。)围攻自动售货餐厅,访问广播电台播音室,参拜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在商店橱窗前流连。他们大都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但有时在纽约,也会碰上失意者——一对青年男女,显然是游客,可能刚刚结婚,他们的灿烂梦想破灭了。这地方让他们吃不消,他们没精打采地坐在一家小馆子里,闷头吃饭,一声儿不吭。
说起纽约,人们听到的一句话经常是:“棒极了,可我讨厌住在那儿。”我感觉,住在乡下和小镇上的人,习惯了方便,习惯了邻里间隔着篱笆和睦相处,想不到纽约生活也有街坊四邻的模式。城市实际上是成千上万个紧凑的居民单位的集合。当然,有大的区和单位:切尔西和默里小丘和格拉默西(居住单位),哈莱姆(种族单位),格林尼治村(热衷艺术和其他事情的单位),还有无线电城(商业开发单位),彼得·库珀村(住宅单位),医疗中心(保健单位)和许多其他部分,各有各的特点。但纽约的事情就妙在,每个大的地理单位都由无数小区组成。每个小区都自给自足。通常,它长不过三两个街区,宽不过几个街区。每个小区都是城中的城中之城。因此,不管你生活在纽约何处,一两个街区内都能找见杂货店、理发店、报摊、擦鞋摊、卖冰卖炭的地下店铺(路过时,可以把你要买的东西写在门外的便笺上)、干洗店、洗衣店、熟食店(啤酒和三明治随时外卖)、花店、殡仪馆、电影院、收音机修理店、文具店、服装店、裁缝铺、药店、泊车场、茶馆、酒吧、五金店、修鞋店。在纽约的大多数小区,每隔一两条街,都有一处小小的商业街。人们清早出门工作,走不上两百码远,就能完成五六件事情:买份报纸;把鞋送到店里钉鞋掌;买盒香烟;订一瓶威士忌吩咐下班时送来;留个字条给煤炭铺的隐身人;通知干洗店有条裤子等着穿。八小时后的回家途中,买一束绒柳、一个马自达灯泡,喝上杯酒,擦擦皮鞋——都在街角下车处与家门之间。这些地面儿事事完备,人们油然而生归属感,许多纽约人一生都守在其中,还大不过一个村子。多走出两个街区,他就仿佛到了异乡,浑身不自在,非得回来。小店的店主对小区的界限尤其敏感。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最近搬家,住进另一处公寓,在三个街区之外。搬家后第二天,她出现在多年来一直光顾的杂货店,店主见到她,激动得几乎落下眼泪。“你这一走,”他说,“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对他来说,三个街区,或者大约七百五十英尺,就是离开了。
我写这篇文章时,就住在纽约的某个小区,过客而已,或是漂泊者,从乡下来此盘桓几日。夏季是个好时光,可以重新打量纽约,领受私密这一馈赠,进入孤独的最高境界。夏天,城里只剩些死硬分子和响当当的角色。(旅游者除外。)临时性的、来去不定的住户没了踪影,惟有货真价实的老纽约。这里的气氛不觉轻松下来,人们只管围块腰布躺倒,一边呼哧哧喘气,一边缅怀往事。我在回想年轻人与大人物同居一城,是怎样一种感觉。我初来纽约时,心中的偶像是十几位专栏作家、评论家和诗人,大名时常出现在报刊上。我始终颇有点兴奋,像是发低烧,因为同一座岛上,还住了唐·马奎斯、海伍德·布龙、克里斯托弗·莫利、富兰克林·P·亚当斯、罗伯特·C·本奇利、弗兰克·沙利文、多萝西·帕克、亚历山大·伍尔科特、林·拉德纳,还有斯蒂芬·文森特·本涅特。我在商会街与百老汇夹角处徘徊,心想:“那座大楼的什么地方,蟑螂阿奇夜里就在打字机键上蹦跳。”那段时期,纽约没给我好日子,但它毕竟让我活下来。
我时常快步走过西十三街第六大道与第七大道之间富兰克林·P·亚当斯的住宅,房子似乎在我脚下颤动,一如火车驶离中央车站时,花园大道也会颤动。这种兴奋(与大人物近在咫尺)是绵延不断的。纽约从来不缺慕名投奔的后生晚辈——青年演员、抱负不凡的年轻诗人、芭蕾舞女演员、画家、记者、歌手,每人都揣了自己的兴奋剂,每人都有自己的一群偶像。纽约不仅给人持续的兴奋,还是个从不谢幕的大舞台。我四下闲逛,重新审视这座舞台,希望能把它写在纸面上。现在是星期六,黄昏时分。我转入西四十八街。从架子鼓和萨克斯管练功房敞开的窗子里,传来音乐教师倦怠的指导声,器乐的嘈杂打破了夏日的沉静。考特剧院涌出日场观众。突然间,整条街响彻一名街头歌手震耳的歌声。他越走越近,寻找知音,是个欢快的黑人,一副唱大歌剧的派头,头颅扬起,恣肆的歌声回荡在高楼壁立的窄街上。长长的手杖,是他惟一的道具,穿着小心而又随意——休闲裤,皱条纹外套,口袋里露出一本书。献艺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考特剧院上演《可敬的妓女》,观众刚刚接受了种族关系教育,急着想要改善黑人的境况。硬币(多是两角五分的)哗啦啦洒向街头,几分钟的游吟,一名黑人的境况有大约八美元的改善。如果每次献艺都能如此,他就完全可以在这里过活了。人们说,纽约是个机会多多的城市。甚至几分钟后迟来的骑警,也信马由缰,在路边踅来踅去,寻找散落的镍币,像鸟儿寻找抛洒的谷子。
现在是七点钟,我再度光顾了东五十三街一家旧日的无照酒吧,准备坐下来吃顿饭。人很少,夏夜电扇的嗡嗡声,偶尔给摇制鸡尾酒的声音打断。小酒吧里黑黢黢的(店主并不认为贩酒法变了,电费就有理由增加)。多么幽暗,多么诱人,渲染意大利湖畔风光的壁画多么绮丽——可能是店主的哪个侄子画的。店主亲手配酒。电扇吟咏祈求风凉的祷文。从另一个隔间传来广播电台主持人的声音,青菜沙拉散发蒜茸的味道。我身后(又是十八英寸),一位年轻文人正试图说服身边的姑娘搬到他那里,做他的恋人。姑娘戒心重重,但他的话入情入理,也并未自视过高。他认为,他们相互之间,应当提供知识与性。从吧台上方的镜子里,我可以看见他们饮了第二轮酒。随后他和她分头去洗手间,两人回来后,争论也无声息了。电扇又嗡嗡地响起来,我又感觉到热浪和轻松的气氛,勾起对许多有趣的非法小馆的记忆,在那里,我曾伴随爱的主题、通风机的声响和杜松子酒消愁止痛的短暂幻觉,多少次津津有味地享用一顿便餐。
另一个溽热的夏夜,我在中央公园林阴道停下脚步,听古德曼管乐队的音乐会。人们坐在乐台前呈扇形排开的长椅上,听得很入神,赞叹不已。林间晚风吹拂,树叶有了活力,哗啦啦地响,像在诉说什么;灯光从下方照亮绿绿的枝条,化作一种新的表达。头顶有飞机悠悠飞过,航灯一闪一闪的。就在我前排的椅子上,少年人坐在那里,搂着他的姑娘,他们相亲相爱,沉浸在音乐中。短号号手走到台前,表演独奏,始于“用你的明眸为我祝酒……”,号声在辽远、温暖的夜空飘荡,那么纯净,那么迷人。随后,从北河那边,传来别一种喇叭的应答——是玛丽女王号邮轮在宣布她的去意。她的独奏与短号不是一个调子,低了半个音阶。乐台上的号手决不示弱。号声吵成一片,没人介意爱的承诺中暗示了远行。“我将远走,”玛丽号在抽泣。“我的眼波会随你驻留,”号手叹息。
大家还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