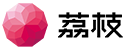介绍:
1979年我第一次离开故乡昆明,受李白的影响,自觉书已经读得差不多了,要顺江东下,云游名山大川。最后去到哪里呢?李白去了长安。那时候中国没有长安,北京是政治中心,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像古代长安那样,诗人云集。或者30年代的上海,一块砖头砸过去,必然砸到文人骚客的脑袋。那时代最匮乏的东西不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太强大了,就是在工厂里的工人,马克思的《资本论》选段也是要学习得唰唰纸响。工厂每年都要搞多次政治学习考试,那论述题是什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还要结合实际,不是死记硬背就完事的。工人在一起开口闭口都是“唯心”“唯物”这些抽象概念,不一定像哲学专家那样明白究竟,但是哲学名词已经成为口语的一部分。最匮乏的东西是物质。当时我还没有考进大学,还在一家工厂工作,以现在的时装标准衡量,我们那时候的形象就是一群破衣烂衫的流浪汉。上海是一个物质中心,上海产,那就是最好的,昆明人以家里拥有的上海货多为荣。长江的终点在上海,我于是来到了上海,那一年我二十五岁。
夏天,我站在南京路上望着那些摩天大厦,心中荡漾着的是青年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我刚刚读完了斯汤达的《红与黑》,于连是我的偶像,我想像中的于连就是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地方。我们在人民公园附近的一家冷饮店里喝了咖啡,很难喝,但在上海喝咖啡,这是我从30年代小说里得到的印象。后来我们决定去一家饭店里豪华地吃一顿,像那些十里洋场的中产阶级。我们走进摩天大楼中的一座,平生第一次穿过旋转门,餐厅里坐着全是穿中山装的人,像是正在开会。我跟着服务员走到其中一张餐桌坐下,菜单就压在玻璃板下面。我瞟了一眼,站起来就跑。那菜单上,最便宜的菜是十三元人民币。吃不起也不至于跑吧?那时候我老害怕着被逮捕,你进入任何一个地方人们都很警惕,戴红袖章的人到处都是,要盘问,要检查工作证。在上海的胡同里,人们已经不习惯陌生人出现,我们偶尔穿过,正在闲聊的老太太就一齐停下,盯着,看你要干什么,然后窃窃私语半天。你走进了一家大饭店——一百万人中只有那么几百个人敢于走进去的大饭店,你坐了下来,却什么也吃不起,这不是很可疑吗?所以我们拔腿就跑,在饭店里的服务员警觉起来之前。幸好没有人出来追我们。一直跑到南京路上,我们才哈哈大笑。
我们每个人身上只带着一百多元人民币,晚上住在火车站,白天旅游。实在不行要住旅馆,也是去住大众浴室,晚上浴室不营业,供浴客休息的床就出租,五毛钱一个床位,还可以洗一澡。只是床是坡形的,躺一下很舒服,长睡就太难受了,但我们总是睡得很香。
南京路上人群密密麻麻,都是来买上海货的,但商品并没有堆积如山,商店并不多,少数的几家店里,挤得水泄不通,也就为了称几斤大白兔奶糖带回去。我们中的一位,第一次出远门,怀里揣着一百多元巨款,缝在内裤上,感觉到处都是小偷。他自告奋勇,总是跟在大家后面,提醒我们这个人很可疑,那个人眼神不对,小心啊,丢了就回不去了。我在一家较小的铺子里买了一双黄皮鞋,二十二元,这种皮鞋我在“红卫兵”抄家的时候看到过一双,但昆明的皮鞋店里的皮鞋都是黑色或棕色的。除了这双皮鞋,我还买了两本书,就是我此行的收获。
晚上,我们去外滩看,外滩在中国相当有名,就像一个传说中的诺亚方舟,名声暧昧,与男女之事有关。去过的人神秘地说,你去了就知道了。而且告诉我们要在八点到十点之间,去早了,人还没有来,去晚了,人就走了,戴红色袖章的人不准大家待到十点以后。我们到了外滩,看呆了,一对对男女面贴面,搂着、抱着、挨着,一对接一对,沿着黄浦江边的栏杆排下去,一眼望不到尽头,就像解放前夕,钞票贬值,南京路上排队换金圆券的人,只是排队的目的不同。大家耳鬓厮磨,喁喁私语,嗡嗡之声像是天空里飞翔着无数的蜜蜂。那个时代这个国家到处是高音喇叭,你在公共场所听见大声的喧哗,那必定是在喊口号、念社论、开庆功会、批判会。公众,居然发出这种声音,我从来没听过,将来恐怕也不会听到第二次。有些人居然抱成一团!没有路灯,黄浦江上有些微弱的光,只看见黑影憧憧,也够令人热血沸腾的啦。在外省,这可能就要被当作流氓抓起来。新来的恋爱者,只有在一旁等着,等先来的恋人谈完走了,才能插进去。我们走了一阵,看别人谈恋爱,很是孤独。
……
热衷于过小日子,在那个时代,是要被鄙视的。我经常听到人们揶揄某人,就说他只会过小日子。过小日子,那就是小市民。谁不是小市民呢?大市民又是谁?好像19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没有鄙夷小市民的传统,市民就是市民,无所谓大小,没有贬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市民社会的颂歌。西方的看法不同,恩格斯揶揄他们民族最伟大的诗人歌德是法兰克福的小市民,“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主张歌颂叱咤风云的无产者,反对歌颂小市民的鄙俗风气。这种思想影响了19世纪以降的世界激进文学,成为时髦。写日常生活的上海作家张爱玲,被许多大文豪视为庸俗。她居然写这些:“苋菜上市的季节,我总是捧着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烧鸭煨汤,汤清而鲜美。烧鸭很小,也不知道是乳鸭还是烧烤过程中缩小的,赭黄的皱皮上毛孔放大了,一粒粒鸡皮疙瘩突出,成为小方块画案。这皮尤其好吃,整个是个洗尽油脂,消瘦净化的烤鸭。”鲁迅当年也住在上海,他住在四川北路。读鲁迅的文章,看不出这是一条怎样的四川北路。今年我又去了上海,到了四川北路,发现那就是过日子的好地方。在一里弄里,我吃到了上好的老鸭粉丝汤,真是美味之至。鲁迅大约对老鸭粉丝汤之类的视而不见,他的文章里从来没有提到,他吃不吃呢?不知道。我想起甘地,奈保尔说,尽管甘地在英国待了三年,他的自传里却丝毫未提及气候或季节,除了到达当天正值九月末,甘地穿着白色法兰绒登岸,因为不适宜而感到尴尬,下一次明确提到的时间,是他离开那天。“没有关于伦敦建筑的描述,没有街道,没有房屋,没有人群,没有公共交通。1890年的伦敦是世界之都,对一个来自印度小镇的年轻人来说,伦敦一定叹为观止。”奈保尔认为甘地“精神内聚是强烈的,自我专注很完整”。“他的体验,发现和誓言,只满足着他自己作为印度教徒的需要,满足在置身敌意中界定并强化自我的需要,它们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奈保尔肯定是这个世界普遍的小市民中的一个,他关心的是生活世界的在场,是日子如何过。他大约会同意张爱玲女士的名言“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20世纪,文豪关心的是“中国向何处去”,宏大叙事成为时代写作的主潮。到“文革”时代,过小日子都已经成为罪行,“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成为革命的对象,革命不是绘画绣花、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暴力成了生活的常态。都热衷于过大日子,大日子怎么过?在广场上,服装一致、万众一心、旗帜招展、高音喇叭。恩格斯的观点只是他的观点而已,并没有使德国成为鄙夷小市民的社会,托马斯·曼、卡夫卡、伯尔⋯⋯这样的小市民作家继续出现并伟大。而在中国,鄙夷小市民却成了人们普遍的价值观,真是可叹!20世纪,人们为主义、观念而活,不为过日子而活。但日子总得过,过日子事关吃喝拉撒,文化上不给这些事情正名,于是小日子总是过得偷偷摸摸、猥琐狼狈。如果不是美国的一位文学批评权威夏志清出来赞美张爱玲,我很怀疑中国读书界是否会认识到张爱玲的不同凡响,在中国20世纪这种文化环境中,张爱玲真的是太另类了!“可以不顾左派理论的影响,安心培养自己的‘风格’。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式的写作,在20世纪的中国确实是独一无二。“文革”之后,继续革命使人厌倦,人们想停下来过过日子,绘画绣花,请客吃饭了,生活的力量卷土重来,西方写小日子的大师,像乔伊斯、普鲁斯特都翻译过来了。但鄙视日常生活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小传统,积习难返,“过小日子”,一时半载是难以名正言顺的。蔑视倒没有了,但无视依然继续,而且麻木不仁,变本加厉。
现代化不幸正是建立在这种普遍地鄙视日常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上。所以我国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很少从居民如何在其中过小日子、如何颐养天年考虑。只考虑宏伟、高大、宽阔、欣欣向荣、金光大道之类的形象,等而次之的则考虑政绩、轰轰烈烈搞一把,高升。考虑经济利益,考虑如何卖掉,房子按照商品房设计。别小看这一点,从家的角度和从商品的角度设计房子是有天渊之别的。古代中国的房子是家,现代则设计成商品房了。政绩也是以高大全的形象是否确立为标准。因此,新世界的建设以摧毁日常生活的小世界为代价,毫不可惜。建立在传统和经验世界上的中国日常生活世界被视为落后、丑陋、丢脸、脏乱差。昆明城市改造,几个月就消灭了七十多个菜市场。新世界建立了,意识形态的象征在现实中得到表现,日常生活世界也消失了。无数故乡消失了,同质化的新世界席卷中国。根据图纸设计出来的形象,面子、观念、商品经济倒是确立了,但不利于过日子。过日子很难看,很庸俗,很丑陋,很脏乱差。张爱玲说,“生命是袭华美的袍,长满了虱子,不要因为虱子忽略了袍子本身的华美”,现在,连袍子都无影无踪了。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0年11月号)
未完待续
大家还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