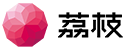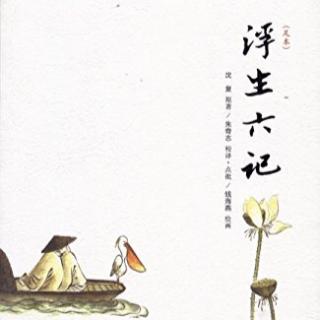
介绍:
今天所读的是闺房记乐的第二部分。书中没有这样的分段,为了朗读方便,我自己按照文意将之分成读起来十分钟左右的段落。
这一部分讲了几件事。一是二人新婚后有过一次短暂的离别,芸是女人,作者三白本来以为她会哭哭啼啼,但芸不是寻常的女人,她不露声色,只是在丈夫临走时小声叮嘱他,这一去没人照料,要自己留心。而这简单的一句嘱咐,其中情意,自是不减常人的啼泣。而三白本人,则是失魂落魄,思念之情,不能自抑。二人重逢之时,更是写得贴切,握手未及开口说话,只觉得“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
二是写两人在家中一个清雅消暑的房子里,饮酒游戏,讨论诗文。两人论述,都非“专业”,但以平常视角看待古今文章词赋,才是生活中真实的雅趣,非学究们动辄据典高谈可比。这里也能看出来芸的聪明诙谐,因为三白说到她喜欢李白的诗,又受白居易琵琶行启蒙识字,嫁了沈三白为妻,一生与白字有缘,芸便巧言,恐怕将来作文要白字连篇。只有聪明人,才开得了这种话里“机锋”的玩笑。
最后,作者还写到,婚后芸娘在言语上举止上都还是十分注意礼貌,三白爽直,不在意这些,本来想劝妻子不要这样,但反被陈芸说到无词,最后只好由她。礼貌之余,两人也十分亲密,在家里家外小地方照面,总要亲昵的拉着手问对方到哪去,有人没人时也总要挨着坐在一起。只有经历过这些细节上的亲昵的人,才能体会在这些细微处,灵魂和身体是在一起的,与你在日常生活中如此亲近的,并非只有爱人的身体,还有他/她的灵魂。
浮生六记 卷一 闺房记乐(二)
芸作新婦,初甚緘默,終日無怒容,與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處下以和,井井然未嘗稍失。每見朝暾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芸曰:「曩之藏粥待君,傳為話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懶惰耳。」余雖戀其臥而德其正,因亦隨之早起。自此耳鬢相磨,親同形影,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
而歡娛易過,轉睫彌月。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專役相迓,受業於武林趙省齋先生門下。先生循循善誘,余今日之尚能握管,先生力也。
歸來完姻時,原訂隨侍到館。聞信之余,心甚悵然,恐芸之對人墮淚。而芸反強顏勸勉,代整行裝,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已。臨行,向余小語曰:「無人調護,自去經心!」
及登舟解纜,正當桃李爭研之候,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群,天地異色。到館後,吾父即渡江東去。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雖時有書來,必兩問一答,中多勉勵詞,余皆浮套語,心殊怏怏。每當風生竹院,月上蕉窗,對景懷人,夢魂顛倒。先生知其情,即致書吾父,出十題而遣余暫歸。喜同戍人得赦。
登舟後,反覺一刻如年。及抵家,吾母處問安畢,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語,而兩人魂魄恍恍然化煙成霧,覺耳中惺然一響,不知更有此身矣。
時當六月,內室炎蒸,幸居滄浪亭愛蓮居西間壁,板橋內一軒臨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纓,濁斯濯足」意也。檐前老樹一株,濃陰覆窗,人面俱綠。隔岸遊人往來不絕。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稟命吾母,攜芸消夏於此。因暑罷繡,終日伴余課書論古,品月評花而已。芸不善飲,強之可三杯,教以射覆為令。自以為人間之樂,無過於此矣。
一日,芸問曰:「各種古文,宗何為是?」余曰:「國策、南華取其靈快,匡衡、劉向取其雅健,史遷、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渾,柳州取其峭,廬陵取其宕,三蘇取其辯,他若賈、董策對,庾、徐駢體,陸贄奏議,取資者不能舉,在人之慧心領會耳。」芸曰:「古文全在識高氣雄,女子學之恐難入彀,唯詩之一道,妾稍有領悟耳。」余曰:「唐以詩取士,而詩之宗匠必推李、杜,卿愛宗何人?」芸發議曰:「杜詩錘煉精純,李詩潇灑落拓。與其學杜之森嚴,不如學李之活潑。」余曰:「工部為詩家之大成,學者多宗之,卿獨取李,何也?」芸曰:「格律謹嚴,詞旨老當,誠杜所獨擅。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愛。非杜亞於李,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愛李心深。」余笑日:「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己。」芸笑曰:「妾尚有啟蒙師自樂天先生,時感於懷,未嘗稍释。」余曰:「何謂也?」芸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余笑曰:「異哉!李太白是知己,自樂天是啟蒙師,余適字三白,為卿婿,卿與『白』字何其有緣耶?」芸笑曰:「白字有緣,將來恐白字連篇耳(吳音呼別字為白字)。」相與大笑。
余曰:「卿既知詩,亦當知賦之棄取。」芸曰:「楚辭為賦之祖,妾學淺費解。就漢、晉人中調高語煉,似覺相如為最。」余戲曰:「當日文君之從長卿,或不在琴而在此乎?」復相與大笑而罷。
余性爽直,落拓不羈;芸若腐儒,迂拘多禮。偶為披衣整袖,必連聲道「得罪」;或遞巾授扇,必起身來接。余始厭之,曰:「卿欲以禮縛我耶?語曰:『禮多必詐』。」芸兩頰發赤,曰:「恭而有禮,何反言詐?」余曰:「恭敬在心,不在虛文。」芸曰:「至親莫如父母,可內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余曰:「前言戲之耳。」芸曰:「世間反目多由戲起,後勿冤妾,令人郁死!」余乃挽之入懷,撫慰之,始解顏為笑。自此「豈敢」、「得罪」竟成語助詞矣。鴻案相莊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
家庭之內,或暗室相逢,窄途邂逅,必握手問曰:「何處去?」私心忒忒,如恐旁人見之者。實則同行並坐,初猶避人,久則不以為意。芸或與人坐談,見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並焉。彼此皆不覺其所以然者,始以為慚,繼成不期然而然。獨怪老年夫婦相視如仇者,不知何意?或日:「非如是,焉得白頭偕老哉?」斯言誠然欽?
大家还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