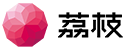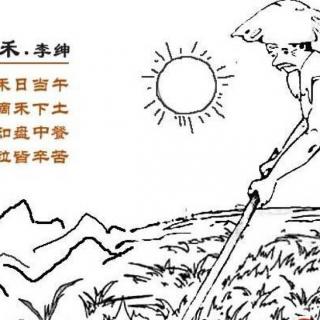
介绍:
空调房里说“双抢”
作者:舟自横
和你们一样,现在的我正呆在空调房里享受着现代化的清凉。而不一样的是,我刚从田里抛秧回来,敲键盘的指甲缝里还留着一些未洗净的黑黑的淤泥。
抛秧是本世纪初才在家乡流行的一项新技术。人们在播早稻的时候会留下一块小田来做晚稻秧田,在早稻收割前二十天左右,把长近两尺、宽尺余的塑料秧模子平铺在扁担宽的畦上,从畦沟里掀些淤泥上来,用套上蛇皮袋的竹扫帚扫平,使秧模子上蜂窝状的小孔里都能有些泥,再均匀地撒上已破胸的稻种。不几天,畦上便泛青了,而秧根全盘在那“小蜂窝”里,这就是秧模子的妙处了:拔时掀起秧模子抖一抖,秧苗便一个个不连根地掉落下来;播时更方便,抓一把秧苗往空中一抛,在重力作用下,苗下连根带土的小团总是先着地。我一个人一天抛个两三亩田是很轻松的,而且这活男女老少都能干,所以即使劳力少的户子,抛秧顶多两三天就可完成。而早稻收割就更快了,收割机割,拖拉机把稻包直接从田头拉到场基上。再加上耙田的工夫,整个“双抢”不过一个星期,离立秋早着呢,哪要“抢”的呀。
过去的“双抢”那才真叫“抢”呢!那时我正是少年,一想起,我的敲键盘的手指都发软了。
先说“抢”收。为了能早点把田耙出来、把秧栽下去,我们村子的做法是“叼稻头子”:拖个大澡盆,盆里放根草绳,用锯齿刀将稻秸齐腰割断,将有稻头的上半部分放在草绳上,打捆后立在田埂上。傍晚时,父亲便把这些“稻把子”一担担地往家门口挑,母亲挑一担回去然后烧晚饭,我和弟弟则继续割。晚饭后,从家里牵个灯泡出来挂在大门口,下一块门板一头担在脱粒机上,一头担在长板凳上,接通电源,便开始给稻头子脱粒了。我把“稻把子”搬到门板上解开草绳,父亲两手不停地往脱粒机里塞稻头子,母亲在另一头掀草,弟弟在脱粒机旁掏稻,一家人就这么分工合作着。这时最让人难受的是蚊虫叮咬,穿长褂长裤也不行,它们叮你的手,叮你的脚,甚至放肆地在你眼皮底下叮你的脸。然后我们还要用大竹筛筛稻,清理场基,父亲则拿着摇把去田里开拖拉机耙田。等他回来,我早已进入了没有梦的梦乡。
第二天,有一个活是较轻松的,那就是继续耙田。昨夜父亲耙的是最难耙的头遍,我则接着耙第二三遍。说这个活较轻松,是因为那时流行使用本县产的“神牛”牌独轮耕整机,前面是个小独轮加个柴油机,中间是个坐凳,后面带犁耙之类。因为能坐着,所以舒服,但父亲总是提醒,千万别睡着了。时常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前一天的劳累,再加上柴油机上冒的烟使人必须眯缝着眼,开着开着,开的人便坐在机子上睡着了,“小独轮”可没睡,它“嗵嗵嗵”地冒着黑烟爬上了田埂,等开机人惊醒拉离合器时,它已在别人家田里了。如果那边是个塘,可就有些危险了。
再说“抢”种。因为稻种直接撒在畦上,所以拔时拖泥带土,速度慢。于是起早,三四点钟被父亲叫醒,半睁睡眼趔趔趄趄往秧田走,真是个“夜半呼儿趁晓耕”啊!“双抢”时你若是看见谁的脚趾用布包着,那准是去秧田时赤脚踢到硬疙瘩了。这时的天还不亮,两旁的田里不见人影,但闻人声。已经有人比我们更早地到秧田里了,“嗵嗵嗵……”,那是在水里垂直上下洗秧的声音,“啪啪啪……”,那是在往腿上敲打秧根上洗不掉的淤泥的声音。父亲为了提高我们的兴趣,总是给我和弟弟每人量几扁担的秧田,说今早把这些拔完就回家吃早饭。而等我们卖力地拔完,也早是日上三竿了。
最吃苦的莫过于栽秧了。首先你得全天弯腰,其次是上下夹攻的热气。天空骄阳似火,晒得后背“冒烟”,脚下水温如汤,熏得满面流汗,白居易的“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便是和这类似的场景了。下手处还时常触到稻桩,拔秧时就已被磨得薄亮的手皮一下就破了,手指破了也还得带上塑料“秧套子”继续栽。如此面朝热水背朝天,一天下来,腰直不起来,眼泡也全浮肿了。
想来点风凉快一下吧,老天自有安排。一般在午后两三点,人们刚下田不久,西天里不经意间起了一片云,你感觉到有风抬头望时,黑云离你头顶就已经不远了。不知谁的一声喊:“抢暴喽!”正在割稻栽秧的人一个个蹦上田埂,手按着头顶的草帽拼命往家跑,场基上还晒着稻呢!家家场基上尘土飞扬,用曳枷拉,用扬耙掀,用扫帚扫,再盖上塑料薄膜,刚用砖头把边角压住,豆大的雨点便噼噼啪啪地在薄膜上开花了。这时,往门槛上一屁股坐倒,手脚发软,全身汗透。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的工夫,太阳又亮晃晃地挂在天上了。继续下田……
整个的“双抢”,从阳历七月十五左右开始,到八月七、八号立秋能干完,就已算快的了。我家年年还要干到秋后一两天。回头想想,那种苦日子不知是怎么过来的。
敲打到这里,我不得不把空调的温度又调高了两度。我在想,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农业技术的不断提高,一定要不到几年,“双抢”这个词汇,也会像“耘耙”、“脱粒机”、“叼稻头子”这些词一样,被更年轻的人所不知道了吧。
2010-8-3
大家还在听